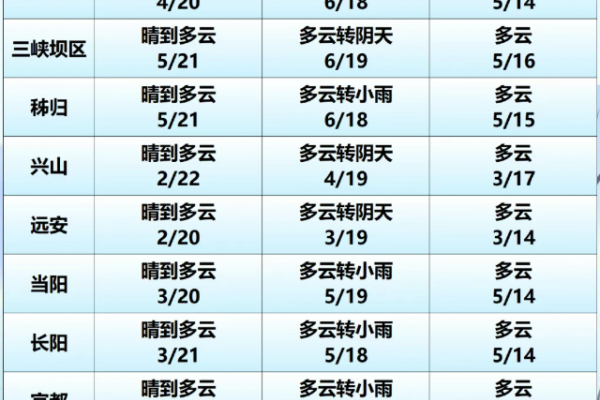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批碉堡、炮楼重回公众视野,它们匿于秭归深山中已大半个世纪。此前,秭归的文史普查人员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并找到了它们。
这些工事是宜昌沦陷后国民党军队为堵截日军进军川东而修筑。它们沿着九畹溪河谷两岸的山坡布防,易守难攻,死死地扼守着日军进川的陆路通道。大半个世纪的岁月让它们失却了当初冷硬锋芒,布满绿苔,隐于荆棘丛中。
二战胜利65周年之际,发现这些抗日工事的秭归九畹溪镇有意把这些工事纳入当地旅游规划之中,也让人们记住那段民族危亡的历史。

8月10日午后,一天中天气醉热的时候。秭归九畹溪镇仙女村支部书记王明山和镇文化干事江勇走在山道上,汗流浃背。
从一条主公路上下来,数百米外的一个山崖叫狮子背,那里有一个炮楼。
走到跟前一股恶臭袭来。进入碉堡的洞口一股粪水流出。“一户人家把牛拴在里面,冬暖夏凉的。”王明山说,没作牛圈前,村民常在里面纳凉,“一个蚊子都没有”。
炮楼是在一个突出的岩体上开凿出来的,貌似一个山洞,4个平方左右。岩体的正上方凿出一尺许的方洞,可以窥探河谷里的动向。“当初洞口是用来架机枪的。”江勇说,此前的田野调查里,有老辈人描述说,曾看到从洞口伸出来粗黑的机枪管,“很吓人”。
捏着鼻子走进炮楼内,踮着脚才能避过脚下的牛粪。岩壁布满了苔绿,壁面凹凸不平,那是当初钢钎在坚硬的岩壁上留下的凿痕,一道连着一道。用手抚摸,岩壁上冰凉冰凉的,有种湿滑的感觉。从炮楼内沿着枪眼往外窥探,葱绿的杂树遮住了视线。这些植被是这两年长出来的,那个时候,视野好得很,河谷里的动向一清二楚。
村里89岁的老人袁前桂见证了这个炮楼修筑过程。当初的施工队就住在他的家里。“一班12个人,他们天天在那里敲啊,砸啊。”
“他们在我家开伙,吃得比我们好。”在袁前桂老人的记忆里,这些兵除了能吃上白米饭外,偶尔还向村民买鸡子杀着吃。令老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些军官的太太们,“她们衣着光鲜在村子里招摇过市。”
当时,在仙女坪村还有一个军队卫生所。战事紧的时候,不断有伤员从前线撤下来,到这里救治。“很多战士死了后就埋在医院旁。”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士兵尸骨文革前被村民刨了。
碉堡群未经战火洗礼
在九畹溪仙女坪村像这样处在山崖上的碉堡、炮楼还有4处。它们藏匿在深山之中,逐渐被世人淡忘。去年,全国文物普查时,江勇发现了这些残留在山里的建筑。
事实上,大山深处的秭归并未遭遇日军战火的涂炭。这里缘何有这么多的现代防御工事?他开始检索资料,实地走访,寻找这些工事的来龙去脉。走访中他发现,这些防御工事沿着九畹溪河谷有很多。它们或是从崖壁上开凿出来,或是用混凝土浇筑,有的是由木料搭建起来。江勇说,它们有的在上个世纪那些疯狂岁月里遭人为砸毁。后来村民们发现这样的建筑结实坚固,是拴牲口的好地方,又用作猪圈、牛棚,有的还成为人的临时居所。当地一户村民,因为“成份不好”在一个炮楼里生活了十几年。
89岁的袁前桂并不能忆起狮子背炮楼的准确时间。“这可能是修得较早的一个炮楼。”根据江勇的考证,这个炮楼修于1938年。
是年6月,日军攻占安庆,武汉会战开始。此后经过长达4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战斗,武汉沦陷,中国军队撤出武汉。湖北省政府迁宜昌,后迁恩施。1940年,宜昌沦陷后,陪都重庆愈加吃紧。为了能够阻止日军铁蹄西进,中国军队加强在长江上的布防。
除加强江防外,国民政府还在陆路加强布防。九畹溪镇位于长江牛肝马肺峡南岸,南接长阳贺家坪,是进入恩施、川东的要道之一。江勇走访调查发现,这些碉堡沿着九畹溪河谷两岸的山坡布防,易守难攻,死死地扼守着日军进川的陆路通道。
但这些固若金汤的设施并未经战火的洗礼。“只有飞机飞过这里,偶尔丢下几枚炸弹。”日军的西进铁蹄被中国军队死死地钳制在宜昌以东。后来的石牌一战彻底阻断了日军西进的步伐,捍卫了陪都重庆,粉碎了日本灭亡中国的美梦。
地下指挥所被后人所砸
沿香溪河谷上溯2公里,江勇带着记者气喘吁吁地爬上了一个山坡。这里小地名叫墓林包,海拔708米。当初是一个埋死人的乱坟包,所以得名。二战期间,中国军队看中了这里,一个地下指挥所就建在这里。
这个历经66年风雨的指挥所呈现在记者面前时已是一个大坑,铜墙铁壁般的顶盖已被掀去。这刚好看清这个不到10个平方小指挥所的设计匠心。
圆坑的四壁光溜溜的,厚重坚实。坑壁上有一排整齐的凹台,是用来放弹匣的。正对着河谷的坑壁上有三个方口。墓林包位于九畹溪、杨林河、西沟河交汇处,视野十分开阔。这三个方口射出去火力如果交织成网,飞鸟都很难逃出这个河口。从地面进入坑内是一个弯曲狭窄的过道,从10多米外慢慢延伸进来。坑壁上有一个孔,指挥所内的人对进来的人一览无遗。江勇说,指挥所设计上十分有匠心。地下指挥所的透气口是个烟囱状的管状东西,设计者将其设计成弯弯曲曲状。“你丢个炸弹也不会掉到室内来。”
“全部用美国进口的‘洋灰’和钢筋浇筑的,牢实得很。”1943年修筑这个地下工事时黄应春4岁。尽管很小,他对这个指挥所的建设情况印象深刻。“我老大还经常到工地上帮忙,我天天跟在屁股后面玩。”黄应春说,差不多一个连的兵力驻在这里。混凝土的材料全部是战士从河里背上来的鹅卵石,另外还征调了当地民夫。混凝土内部布满了12号螺纹钢。
“石壁这么光滑不是一二次粉刷弄出来的,他们的工艺很好。”黄应春说,修筑时战士们把一棵大树砍了,锯成光滑木板用来支模。工期一直从1943年的10月到1944年的3月结束。所有施工结束后,他们又在指挥所的顶上堆放封土,为了伪装,在上面还栽了几棵树。
这个固若金汤的工事在战争中逃过了一劫,却没有逃过和平年代群众的打砸。解放后,群众除去指挥所上面的封土,把屋顶作为晒谷场。1958年大炼钢铁,群众发现混凝土里的钢筋。于是锤砸、炸药炸,屋顶终于被掀去。“群众实在没有办法弄出坑壁里的钢筋,这才让它逃过一劫。”
在文物普查后,九畹溪镇的碉堡群已上报给了文物部门。“这里正好在九畹溪景区里,政府想把它纳入到景区规划里。”江勇说,如果有钱,把这些工事修复起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好。